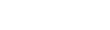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悬空观。
一年日头里最毒日子,钟鼎性躁,耐不住热,一早赖进厢房躲懒。
原也不是来客的好时候,偏就这一亩三分的清闲地,还总有几个不开眼的隔三差五传书递信。
“钟阿娘,前头又进信。”白胖圆脸的阿圆崽一掌划地,缩着脖子趴在他暴脾气老娘门前,小心翼翼碎碎念叨:“前头攒了一堆,快有半个树墩儿高了,阿娘若不瞧,留着也积灰,阿圆都吞了去。”
钟鼎瘫在躺椅上,鬼天气真是挪一步就会化为原型的热,她哑着嗓子有气无力地应:“麻溜,别让我瞧见。”
阿圆抠了抠他光溜溜的圆脑袋,犹豫又彷徨:“可是,绿绿哥哥刚刚又来一封。”
“......”
“新的,邮戳印的是曲商。”
“......”
钟鼎强忍脾气,眼前巨幅的“忍”字并没有令她领悟到几分心静自然凉,她只重新将手插回不再冰凉的水里,告诫自己发火只会更热,要冷静,冷静。
......冷静个屁!她骂骂咧咧:“一个不留。”
“可信上还有阿爷的气息。”阿圆撑着把最后半句气音挤出来:“......新鲜得很。”
这头气音才飘落下,下一弹指,木板门就被大力踹开,“咚”的一声重重砸在阿圆脸上
走出的这位施暴者一脸黑的火气,怒发冲冠,剑拔弩张,阿圆心惊肉跳。
施暴者捏着阿圆递来的一叠信,约摸厚度,真是好大手笔。她嘴里念着阴阳怪气的话,“当初那些个事不关己,如今倒搭起戏台,真是把自己感动坏了。”
阿圆“啵”地狠狠将脸从门里拔出来,一阵肉痛地看着被撞出“脸”形的木板门,抬手就“哐哐”拍打着木门,妄想能敲平它。
他胸腔发麻,仿佛还能听到又一笔钱翘首回望、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远去的脚步声,眼眶发热心疼道:“阿娘可要回个口信?阿圆就在这儿等。”顺便哭一场。
钟鼎抬头望着明晃晃的日头,一晃眼又被阿圆油光锃亮的脑袋气得火气更甚,她道:“知道你是个不惧热浪的,搁我这儿做哪门子的光合作用,你老娘一脑袋的火,挪外头哭去。”又磨了磨牙,没好气地吼:“滚远些。”
阿圆摸了摸又被甩上的门板,“呜呜”地吸溜鼻音,自我安慰道:“不疼不疼。”不知是心疼门板多些还是心疼捂不热乎的钱袋子多些。
甩上门的钟鼎随手将废纸扔在几案上,动作粗鲁,甚至小部分被甩进水缸里。阿圆说得没错,老头的气息很重,但这东西不可能是老头的亲笔。
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搞诈尸,可笑。
屁话恭维三两眼一扫过,一封又一封地随便扒拉,钟鼎丝毫不浪费时间。一摞的信大同小异,这个说大厦倾塌,那个谈九州多变,谁不明眼看着,用得着来指教,不过是美谈空谈的屁话。
废纸满满丢了一地,只余下最特殊的迟迟未动手。钟鼎扭头从兜里掏出个钢镚,插不插手闲事就看它的。
然后便抛了个菊花面......呵,实在好样的。
钟鼎随手把大功臣钢镚兄立在案上,一把把信揣进怀里,不带半分停歇又一踹门,顶着烈日和一身火气往后院跑。
这观原本也不是观,更不是供奉的地,从鼎盛到现在的残喘也不过百年光阴,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后院处地不大,可供休憩的厢房一排半塌,没钱修缮它。原来的钟楼鼓楼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