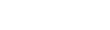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浩山:
这一刻,你会不会皱着眉头,心里觉得很奇怪,从来不写信的我,为什么竟会在你离开一年之后拿起笔写信给你?
你现在离我有十万八千里远吧?还是更远?这些信,要是没寄出去的话,写给你,也就是写给我自己。
距离那么远,任凭我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你去的那个非洲小国始终有点不真实,给你写信,就好像我是躺在非洲蛮荒的大片草原上,跟你两个人,像我们小时候,也像从前一样,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地说着话,分享着彼此的秘密,然后,也许只记得那些秘密,却忘了大部分说过的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一天,尽管我们已经各奔东西,想起当时的对话,我们还是会微笑或是沉思。
可是,假使这一切到头来只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你没回信,那我只好猜想你已经不幸成为狮子腹中的大餐或是被非洲食人族吃掉(我不知道哪样更惨?)。你永远收不到我的信,而不是你再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虽然我能够理解你的理由。你实在有一千个理由不再理我。)
我是不是又在自我安慰了?还是你正在心里咕哝:
"她这个人还真够无赖,她一直都是个无赖。"
怎么都好,写信给一个断绝了一切现代通讯工具的人,本来就有点像自说自话的吧?
五个月前,父亲离开了。
那时候,我绝对没法想象我可以这样平静地告诉你,甚至还能够坐在这里跟你说笑。
出事的那一天,火锅店午夜打烊之后,他一如往常地徒步回家。回家的寂静的路上,这个世上最爱我的、陪伴了我二十四年的男人孤零零地昏倒在路边,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医院的太平间,苍白的身躯上覆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夹克,那是他中午离家时穿的,左边脸颊的瘀伤是昏倒时造成的。
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相信他离开了我。他才只有五十九岁,外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年纪年轻许多,虽然个子不高,却也英俊潇洒。呵呵,我是不是有点恋父?可惜,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全都不像他,没他长得好看。遗传这东西真会作弄人啊!
父亲是死于脑部一个像气泡般微小的血管瘤破裂。这个病,事前毫无征兆,在短短一瞬间就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我可怜的父亲根本不知道他脑袋里长了一个随时会把他炸掉的小气泡。后来,我常常想,那个充血的气泡"啵"的一声破裂的时候,也许就像粉红香槟里飘散的幻灭的泡沫,那么美丽,谁又会想到它是来谋杀你的?
我母亲爱死粉红香槟了。我喝的第一口酒就是它。那年我九岁,父母让我自己捧着一只冰凉的长脚杯尝尝那酒的滋味。瞧瞧他们到底怎么当父母的?竟然让一个小女孩喝酒而不是橘子汁。
等我长大到可以喝酒的时候,我老是拿这件事情来埋怨我的父亲虐待我,我们父女俩偶尔会在吃饭时开一瓶"酩悦"粉红香槟,喝着酒,纪念我早逝的母亲。
但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想喝它了。
七月底那个尘烟漫漫的星期四,父亲被放到一个墓穴里,工人在他身上覆盖厚厚的泥土,把他埋骨在他妻子身畔。我的父母以这种形式长相厮守。从那天起,我彻底成为一个孤儿。
那天的烈日晒得我的头昏昏的,我穿在身上的丧服、我的皮肤、我的头发、我的眼睛,全都被汗水湿透。你一定在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