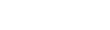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悒——我决定了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意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画,也想看一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时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似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借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催促我快还这些心愿。
二十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