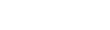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那年,寒天冻日头地冷,西北风掠过地面,连个草渣子都没剩下,庄子里的榆树成了光杆杆,白生生的,树皮叫人剥下来捣碎煮熟吃了,天上飞的雀儿、地上跑的老鼠子都不见一个,庄子里没个生气。
死了人,开始还有个白皮子棺材,抬到祖坟里埋了,活人也哭嚎几声,后头一个接一个的死,席巴子一卷就撂到大河坝里,活人也就没有了嚎声,人阿都饿的恓惶惶地,放下是一滩泥,提起来是一条肉,活人都顾不上,哪里顾得上死人,奈何桥上,人一半的鬼一半呐。
清早起来,狗朝地埂子使劲的叫,地埂子下面爬出来两个血斯呼喇的丫头子,才十六七岁,给些热水喝完,就朝着山里头跑了,后来听说倪家营子打仗,一伙学生兵打败了,顺着这条路钻山哩。
也日怪,那年狼多的很,不知道是打哪里来的。
——————老人的一段话。
那个岁月,到处都是炼狱般的苦难。人在兽群里挣扎着,拼了性命找寻自己认定的信仰、公平、正义,就是想活的像个人。
八声甘州
第一声
一
罗望眯着眼朝西望了一眼,见日头已搁在山尖上,就对车里的人说:“娘,咱进城吧,再迟要关城门哩,”席篷车里的女人只应了一个字:“嗯。”
娘俩确定不走了,在这里落脚是下午的事。就在远远的看到城门时,罗望吆住马,让母亲下车吃点东西,母亲下车,吃了几口石子馍,喝几口水,就到池塘边看儿子饮牲口,她沿着池塘边走了一会。回到儿子身边,一边牵住马让儿子洗刷,一边问:“望儿,这是啥地界,这海子,芦苇,有些好哩。”罗望明白母亲的心思,这是不想走了。他已经在问路时打听了,这里是甘州。一路上尽是黄沙、戈壁、光秃秃的山包,看到这里远处的山峦、面前的池塘,郁郁葱葱的芦苇,还真有几分老家的味道。他觉得应该到了停脚的地方了吧,就这样,娘俩一合计,落脚甘州。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往往都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发生,决定一个人往后的生活,演绎出精彩的、苦难的百味人生,世事无常,大抵如此。逃难的罗望母子就在民国20年(1931年)深秋的黄昏,赶一辆席篷马车,在落日的余晖里走进了未知。
罗望套好马,招呼母亲上车坐好,吆马徐徐走向城门,城门口已经没有人进出,守门的一个士卒坐在石墩子上吃水烟(抽水烟),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搭理进城的车子。
进城不远,看见一皂布白字的幌子上写着“席福大车店,”门边的榆树旁蹲着一汉子,两手捧一老碗(大海碗)在舔,脸遮住了,只露出灰黑的大脑袋,直到罗望把马车停在跟前,才把碗放地上,站起来招呼:“老客,住下吧,城里最好的店哩,”他站起来比蹲着高不了多少,是个背锅,硕大的头颅,双臂长于常人,声音却很尖细,叫了一声:“婆姨,来客哩,”从砖房的第一间出来一中年女人,人高马大的,脸庞周正,粗眉大眼,嗓音却粗,“哟,老客,是两个人吧,车里是,”停住不往下说,眼睛瞅着罗望,罗望赶紧的说:“是我娘,”“好嘀哩好嘀哩,店里正有一个套间,里外都能睡人。”
罗望明白,这老板娘外粗内秀,能从席篷车判断出是两个人,而且车上是女的,才停住话,等着罗望说出车上人的身份,免得闹出笑话。眼见天色已暗,罗望打算住下再说。母亲也下了车,看了老板夫妻几眼说:“就这儿吧,”老板娘马上应声:“好嘞。”
天黑下来了,老板夫妻两人端来两碗粥,虽然罗望看见背锅老板舔碗,这会端来的也是一样的大海碗,他没言声端起了海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