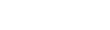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傍晚时分,陈鸿晴要准备烧晚饭了,看郑明一天到晚捧着一本书不放,想找个理由让他起身活动活动,以免看晕了他那老脑子,就高声对他说:“老郑,晚上家里该买点豆腐了,你出去看看。”他只“嗳”了一声,还不肯放下手中的书,不过他的耳朵已开始竖起来捕捉街上叫卖豆腐的吆喝声。
陈鸿晴已经进了厨房,没再催他。他们的生活很默契,心有灵犀一点通,相互间极其理解和包容,很单纯很电影式。没过多久,伴随着板车在路上发出的“咯楞咯楞”声,随即那再熟悉不过的“卖豆腐”的叫卖声也响了过来。“买豆腐啦,买豆腐啦!”
郑明一听叫到卖声,立即站起身到碗柜里拿了一只大瓷碗,就向门外走去。
卖豆腐的中年男子一来,小巷里顿时就热闹了,守在家里的老人和媳妇们也陆续走出门来,相互打着招呼,每个人都习惯了在这个时候,等待豆腐车的到来。
卖豆腐的中年男子,听说原来是个外乡人。他做豆腐技术是祖传的,参的是盐卤,它的工艺和口味是新岭乡最好的,虽然,看上去没其它工艺的细嫩,但韧性好,不论是煎、煮,还是炸,口感都特别好。他的豆腐到新岭一上市,就被豆腐民们爱上了,买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地就习惯了,甚至吃上了瘾。
只是每个到他这里买过豆腐的人,都会对他的模样感到好奇。他高大而粗壮,厚嘴唇,鼻翼宽大。他的手掌大而粗糙,手指尖到指肚都是一样的粗,也许是因为干多了活的缘故,每个手指头都方楞楞的,显得很笨拙,可能是皮肤黑,手掌心比手背肤色淡很多,像非洲的黑人。在普遍个头不高,身材单薄的南方水乡人的眼里,他的样子,有点格格不入。单从外表来看,就知道他是一个能干粗活的人。
卖豆腐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天他都是这样叫喊着出来卖豆腐,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维持着他简单的生活。大家已经记不清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卖豆腐了,他的样子似乎也一直没有变化。仔细一看,却着实比早些年消瘦了很多,他的车子也老旧不堪了。时代的车轮,在他,和他的车子身上都毫不留情地留下了碾压的痕迹。只有他摊子上的豆腐,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新鲜白嫩,似乎时光在此驻足不前了。
此时,和往常一样,卖豆腐的男子站在小板车边上,车上摆着一板新鲜的豆腐,豆腐刚出锅,在**的纱布下冒着热气。他只是低着头,用锃亮的黄铜板子,切下一块块豆腐,再用板子托着,把颤巍巍的豆腐放到各人的碗里。白嫩的豆腐和他粗糙发黄的手掌极不相称,偏偏他和豆腐相依为命。他的本分是出了名的,连买菜时要扒拉秤砣看秤星的精明主妇也在他称重时扭头和别人说笑,不怕秤被做了手脚。偶尔有人对他说几句玩笑话,故意交代他秤要足,别缺斤少两,边上的人都嬉笑起来,他也只是勉强牵扯一下嘴角,挤出一丝笑来。和热闹的人群相比,他是木讷的,生活的艰辛压得他日渐麻木,远离欢笑。
这时,一个衣着寒酸,面色灰黄的妇女走近豆腐摊。这是个不幸的女人,家里丈夫早逝,她一边供两个儿女读书,一边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家里的艰辛可想而知。她极少买时新蔬菜,吃的都是自家腌的咸菜,平日里是难得花上几毛钱买豆腐的,很多主妇都曾见过她在菜市场捡过菜帮子。人群蓦然安静了下来。这个妇女有点难为情地和邻居打着招呼:“嗳,你也在啊。我家婆婆身体不好,老人家想吃豆腐了。”又转头对卖豆腐的说:“帮我切两毛钱的豆腐。”卖豆腐的男子略一迟疑,便麻利地切下一大块豆腐,称也不称,就放入妇女碗里,边上有人笑起来:“还没称哪!生意太好,高兴糊涂啦?”
他却低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