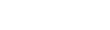点击一下,解锁更多精彩小说
新作《船帮老大》,我差不多已经酝酿筹谋了近16年了。
1998年的年底,我参加文联作协联合举办的一个笔会,其间,接触了一位写散文的朋友,他的爷爷曾经在汉江上跑船,为他讲述过太多关于汉江船帮的故事,类如仅凭一舟、一鱼叉,便可在江上叉鱼,一天时间,满载而归;类如每年桃花盛开,船帮举行开航仪式,大碗喝酒,高唱船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解缆开航,等等等等……
他为我转述这些细节之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如今的汉江,因为下游兴建水电站,早已不再通航,我想用文字复原曾经繁盛的船帮景象。胸膛中跳动着的创作热情,蓬勃不止!于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许多地方,探寻了诸多秘辛,从民国时期的江湖奇闻,到汉江沿岸的民俗文化,从贾平凹先生故乡的船帮会馆,到襄阳武汉的许多船帮故纸资料,从青帮、袍哥的帮派文化,到整个陕南鄂西的棒客传奇,从重庆纤夫的歌谣,到茶铺里打纸页牌的老人们口中的旧事典故……
2000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节,我曾在汉江边摆下三块圆溜溜的白色鹅卵石,在沙滩上写下“船帮老大”四个大字,面对滚滚东去的汉江水,俯身而跪,拱手以拜,决定要开始写这本书了……
然而,天地之间,万法随缘,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事与事,物与物,莫不如此!一切皆是缘分,一切终有定数!
我严重低估了创作的难度,同时,又严重高估了我的笔力。那时候,我还是用圆珠笔在纸上写作,在写完了两支圆珠笔,写废了一大堆用白纸线订的草稿本后,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和怅然若失之中,写了撕,撕了写,始终感觉不对味道,尤其是主角的形象,始终是一片模糊,仿佛是一尊刚刚拓了形的石佛,虽然大体得出,但面目气质,神情细节,全然无痕无迹――这,怎么能写?怎么能写的下去?即便拼了命地写了,又如何能入读者法眼?
因为这一次的创作失败,我进入了一种“畏惧创作”的恶性循环当中,一年又一年过去,我结婚、生子,工作,生活,任时间将我一再雕琢,青涩已去,不再年轻……然而,对于《船帮老大》,拒心有不甘,但始终未能起笔。
我在无数次的审视反省中,探寻着许多创作的玄机,一本又一本地读书,一本又一本地写着读书笔记,渐渐发现――原来,我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创作的角度,确切说,我没有将《船帮老大》的主角,想清楚,想透彻,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他的语调,他的身形,他的衣着,他的眼眸,他的方方面面,我都没有想到,我怎么能写?
有一个冬夜,我坐在被窝里,重读李渔的《闲情偶寄》,读到“结构第一”之“立主脑”――“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只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只为一事而设。引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
我几乎从被窝里跳了出来,一连抽了半包烟,终于向自己确认――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深受困惑的根源,这也正是我苦苦探寻的终极真髓,无边法门啊!
不再高估,不再低估,青涩早去,惟有淡然……当一切都过去,一切,都将衰朽,惟有那些文字,文字之下的情怀,永远鲜亮!
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我终于开始了。
在键盘的噼啪声里,汗流浃背,内心时常冲荡着一种莫名的沧桑和悲壮,但转而,却是欣然,亦是浑化。
这便是那种缘分,归宿感,宿命感,自此之后,一直在我指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